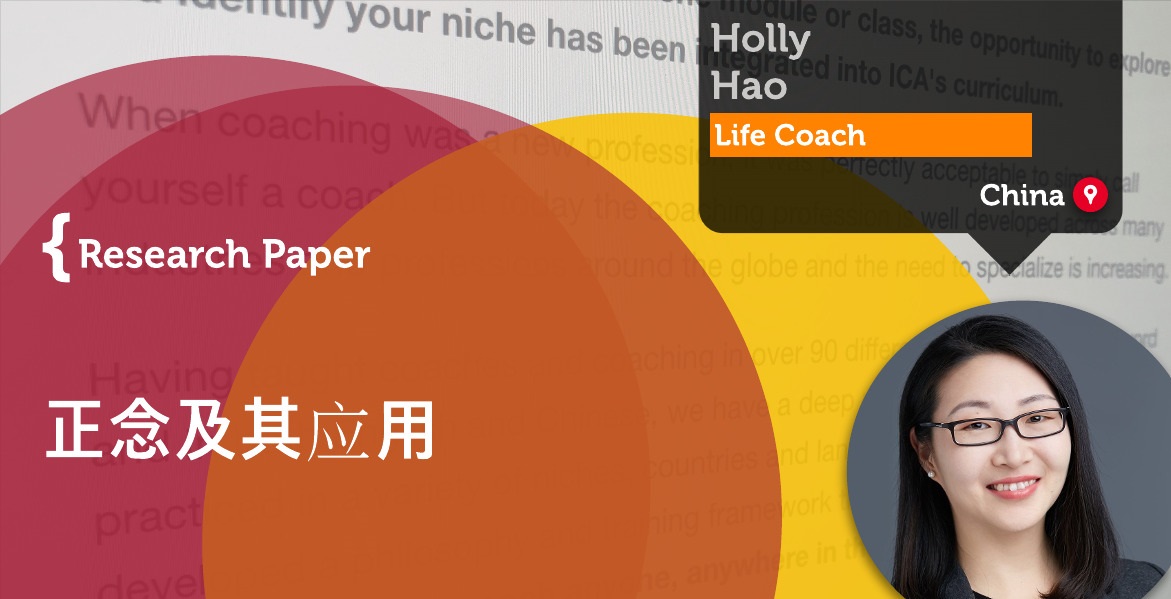 A Research Paper Created by Holly Hao
A Research Paper Created by Holly Hao
(Life Coach, CHINA)
 开始学习教练之后,在练习中时不时的会被要求“闭上眼,做几个深呼吸”“在呼吸中感受你的情绪”“试着与自己连接”……开始面对教练或老师提出的这种要求,心里总犯着嘀咕带着些许不情愿。每次总是敷衍着闭上眼,匆匆呼吸,然后偷偷睁眼看看教练、老师、其他人都在干嘛。深呼吸、感受、链接…..统统不存在。
开始学习教练之后,在练习中时不时的会被要求“闭上眼,做几个深呼吸”“在呼吸中感受你的情绪”“试着与自己连接”……开始面对教练或老师提出的这种要求,心里总犯着嘀咕带着些许不情愿。每次总是敷衍着闭上眼,匆匆呼吸,然后偷偷睁眼看看教练、老师、其他人都在干嘛。深呼吸、感受、链接…..统统不存在。
一个机缘巧合的机会加入了一个高质量读书会,开始的第一本书便是乔恩·卡巴金的《多舛的生命:正念疗愈帮你抚平压力、疼痛和创伤》。
令人意外的是,读书会活动并不是一起看书或分享书中内容,而是进行了一次mindfuleating的练习——正念吃葡萄干。虽然曾经吃过无数个葡萄干,但这一次感觉却像是生命中第一次真正见到并吃到葡萄干。拿在手里仔细端�